曾经有人说,曹斐的作品是为了迎合西方审美而创作的,
她回怼:“我的艺术是自助餐,并不是为谁创造的。”
对于艺术领域来说,曹斐像是一个“野路子”,浑身充满着对僵化体制的不满——那股叛逆,像极了朋克。

实境:整个系统让我们收敛情感,但我对此感到厌倦
纵观曹斐作品中的人物,都在一开始存在一种难以置信的隐忍。《谁的乌托邦》里的灯泡厂工人,《霾》里去看房子的年轻人,以及高楼中的一对夫妇……
细细品,他们的隐忍其实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。然而这种隐忍绝对会在某一时刻,你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。是呐喊,也是绽放。

《我的未来不是梦 My Future is Not a Dream 》
就像是挤破了的脓包。浓水流出的那一刻,有什么东西被破除了,伤口也开始愈合了。
还记得有个微博热搜:#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——被查到酒驾的男人抱着警察哭诉,也看到快递小哥在街头抱头痛哭……

但,崩溃真的就在一瞬间吗?
当我们赶不上时代发展的速度时,会变得越发麻木,一味地追赶,追赶,追赶……即使曾想过活成自己,却担心自己的人生耽搁在寻找的路上。
时间的有限性带给现代人太多的恐惧,让我们不得不选择屈服于这具“行尸”般的肉体。
我们害怕“社死”,不希望别人说自己“情绪化”……一切的情绪被这个社会视为“无能”,“低效”的表现。
于是为了迎合资本社会的快速运转,我们选择压抑原本合理的情绪,等到最后一刻才发现,原来自己已经忍了太久。
然而,人活在这世上需要有一些出口的——成年人需要学会把有毒的脓包挤破,让伤口自我疗愈。
对有的人来说,出口是狂放的朋克,而对曹斐来说,是她的艺术作品。

虚境:人民城寨——对日常生活的抵抗
我们花大部分时间做一个社会认为的“正常人”,局限于自己的职业舞台,家庭舞台……但曹斐选择把视角放宽,她选择不断的重塑舞台,重塑每个人的可能性……
当现实世界的出口慢慢缩窄,人们逐渐被另一个可能吸引。那是一个个陌生人组成的另一个世界。
虚拟世界就是另一个出口。
ARG(Alternative Reality Game)游戏出现后,虚拟环境更是慢慢成为人们寻找慰藉的另外一个空间。《第二人生》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人类有限幻想的真实存在的游戏。
你说它虚拟?那里却存在真实的情感和关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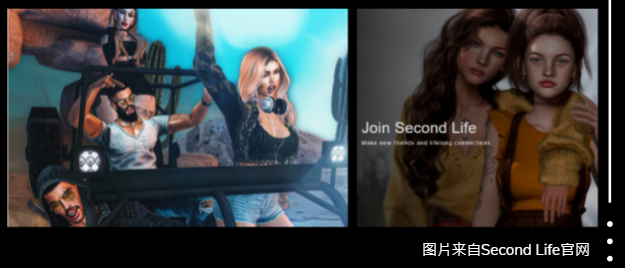
只是人们不再害怕社死,不再有社交上的负担。在那里,每个人都可以“重活一次”。

而这一次,你有机会活成自己最洒脱的样子。
打开游戏官网,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都给人一种“老子就是山大王”的感觉。
曹斐就基于这样一个系统,搭建了自己的《人民城寨》项目。
五年的时间,曹斐带着“田野观察”的心态和一直以来的好奇心全然进入了一个从未接触过的领域,用“中国翠西”(China Tracy)的虚拟身份尝试在一个异度空间建立现代化虚拟都市。

当她慢慢建构完善,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外国对于中国刻板印象的拼接,和一个符合现代人语境的“中国城”。
在那里,她遇到了弹钢琴的虚拟帅哥,也展开了一段似实或虚的情感纠缠。
他们所做的事都的的确确的存在且发生了,只不过在现实是生活中,那位“帅哥”是一位曾经吃了几十年牢饭的60岁老人。
说来可笑,但这现实听起来,是不是比虚拟还不真实?
舞:过剩信息创造了“虚无”,她只能不断寻找自己的舞台
曹斐就这样通过作品在现实与虚拟中游走。当现在与未来逐渐靠近,实境与虚境的界限也在她的预言下逐渐模糊。
但就像她所认为的,“人类的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”,未来也许会倒退成过去,过去也有可能是将来——所以实、虚或许并本不存在所谓的界限。

所有的界限都是人类的语言所创立的——就是那座巴别塔,把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复杂化,让我们处于到处充满界限的世界里,各自“二元化”。
于是矛盾产生了。
语言上的二元划分——“男/女,东/西,虚/实……”,本身就是外界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捆绑。而任何将事情一分为二的态度、视角、想法,都是人类语言的惰性。
在一次采访中,曹斐曾表示对这种性别意识惰性的反抗:“你无论做了多少努力,别人都会把你归为,你是女性。”
当这个世界的信息太过复杂,很多人懒得去思考,懒得去反抗,于是愈发活在框架里,“画地为牢”,“作茧自缚”。而曹斐可以通过艺术,游走在那些所谓的界限当中,用艺术去解构,去破除,去铺开,去延伸。
人们说曹斐的作品有别于其他学术派的艺术作品,是有创新意义的。
但“创新”到底是什么呢?
那从来不是空穴来风的想象,而是对时代敏感的观察。
我们是被时代裹挟的一代,被动的接受“二手的信息”。我们失去了观察的能力,自然也就离创新越来越远。
曹斐却很巧妙的跳出了时针,静静地观察我们的运作:“我们沉溺在信息的海洋中,在创造的时候咀嚼同样的信息,最后再吐出你自己消化后的信息,它不就是一个闭环吗?”
因此,她永远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表达的出口。无论是电炮工厂,二次人生,还是与朋克的跨界合作,她总是试图找到新的落脚点,选择用艺术摆脱顽固且僵化的语言体系,尝试实现表达的自由。

作为艺术家,她的作品无论是对“实”的质疑,还是对“虚”的探索,都充斥着对于二者间界限的叛逆态度;
作为艺术评论,她不喜欢一些策展人将艺术置于高台,也曾建议艺术生不要去应试学习固定套路的雕塑,因为那些都是学术带来的限制;
作为女性,她也不局限于女性身份,在女人、母亲的角色舞台中,她四处张望,四处探索,尝试活出最多杨的自己。
她的一切都在破除,是“虚无主义”的绝对实践,也是这个时代缺少的“朋克精神”。







